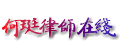南方人物周刊:赵本山的江湖
1247 人阅读 日期:2009-02-24 18:28:21 作者/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沈阳
“来啦?”“来了。”
下装(男,丑角)完成一段说口,探了探当晚台下的“水温”,以不带重样的说法,比如“上菜”、“提车”,将自己那半副架(女搭档,行话叫“上装”)从后台引上来,少不得让观众“给点儿薄面,掌声!”这边招呼琴师“走嘞”,与时俱进的二人转小帽、扮、唱、绝活随即展开。
每晚五码戏,每码25-30分钟。在各自时段里,台上二人“胜似千军万马”,京戏、杂技、绕口令无所不能,“刘欢”、“张雨生”、“阿宝”、“印度舞娘”轮番登场,当然,搞笑是必须的。他们大方、松弛、自来熟,一码终了,额上浮出一层密密的汗珠,若滚落下来,自有台上那块厚厚的、近百平方米的地毯接着。近800位观众在宜人的暖气里,就着饮料爆米花,每隔三五分钟笑成一浪一浪,跟风吹高粱地似的。
这是2月10日、11日两晚,记者在沈阳中街刘老根大舞台看到的21世纪新型“绿色”二人转。舞台红艳艳的,两侧大屏幕不断打出电子条幅:祝贺小品《不差钱》荣获2009春晚语言类一等奖;祝贺赵本山董事长第14次摘取春晚“小品王”。六七位高个、清瘦、黑衣的保安戴着耳机,巡视在门廊之间,像大片里一样。
11日晚大约9时,据说元宵节后被安排在湖北四川跑场、不到3月初回不了沈阳的小沈阳突然出现在大舞台上,唱底包(压轴)。还是春晚那身行头,白衣、穿跑偏的“苏格兰裙裤”;还是那个调调,“准备好了么,mu~sic”。这天晚上,走廊里多了十来个加座,每座300元。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厅观众,是按楼层、排数、中间还是两旁的10种划分,分别掏150-460元进场的;5个包厢,排出2200、2400、2600三种价——这是记者见过的最精细的价目表。
接连两晚散场时,微恙、因而脸色不大好的赵本山从二楼包厢下来,皮衣皮帽,黑白细纹羊绒围巾,淡淡香水味。他被簇拥,被保护,被剧场门口年轻的女孩们等待。当他坐进那辆车牌号出租车司机一眼就能认出的“帝王”,女孩们仍在挥手,有一位还将手掌贴上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车窗。昏暗中,只见车里送过来一只手掌的轮廓,印在车窗上,摇了摇。
徒弟们也一个个驾车走了,从头码到底包,车价渐高。据懂车的人说,头晚压轴、小沈阳回来后唱四码的王小利(《乡村爱情2》中饰刘能)的座驾60多万,小沈阳的途锐100多万,车牌号是他的出生年份。
随着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关东大先生》的播出,沈阳人多半能一眼认出从这个舞台上走来的演员:“哎,这不那谁嘛!”
这种打着“刘老根”字号的舞台,在沈阳市区有3家,本溪市2008年底新开张一家,吉林、长春、天津各一家。赵本山在受访时告诉记者,北京的刘老根大舞台计划5月1号开业,而传闻中上海、南京等地的连锁店,“有可能(开)”。
创家业
从南方到北方,从在电视上认识他的人到在生活中认识他的人,随着离赵本山越来越近,滋味也复杂起来。对他身份的认定在渐变:“小品王”、“唱二人转出身的演员”、“超级农民”、“上过2次福布斯富豪榜的企业家”、“江湖霸主”、“师傅”;他的口碑与形象也在渐变:“朴实”、“本色”、“太逗了”、“一身是艺”、“不好打交道”、“霸道”、“人挺好的”、“真不好说”。
1978年,赵本山从辽宁铁岭开原县莲花乡石嘴沟村走出来,走了30年,走出今天的局面。目前他出任本山传媒集团董事长,下设1个总裁、8个副总裁、1个工会主席。从本山影视基地通告栏里张布的09年分工,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家业:
总裁刘双平,分管旗下辽宁民间艺术团、中街大舞台及其他连锁剧场、辽宁大学本山艺术学院;常务副总裁马瑞东分管瑞东公司、人力资源部、北京剧场、舞美等;副总裁魏国负责财务及票务;刘流分管电视剧、电视栏目、发行及广告;徐正超负责艺术创作;刘文田负责物业、外保、安全;张家豪分管演出;孙超负责宣传与相关对外事务。
刘双平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央歌舞团团长助理。马瑞东是赵本山妻子马丽娟的弟弟。刘流,相声演员,在《乡村爱情2》中演“刘大脑袋”,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中给白云大妈、黑土大伯递火炬那个主持人。徐正超,原《时代商报》记者,后拜崔凯为师,想走专业创作道路。张家豪,在《乡村爱情2》中演“豪哥”,原名张建设,曾是石家庄名人,“霸气与生俱来”,有多年娱乐夜场的从业经验,小沈阳从哈尔滨转至刘老根大舞台,他是伯乐。据说他是赵本山前经纪人赵钢引荐入集团的,而后将一些穿黑衣的大个子带到赵本山身边……“英雄不问来路”,这些在另一处也许永远无缘做同事的人如今聚在赵氏门下,各司其职。赵本山用人的豪迈可见一斑。
在2009年集团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班子一律肥袄布鞋,头戴小帽,帽沿缀朵小花,集体表演歌舞小品《小草》,扮相貌似董事长当年,神态却南辕北辙——“与民同乐”的效果是达到了。赵本山这种不分上下你我的亲和劲儿,也贯彻到一对龙凤胎身上,12岁的牛牛和妞妞也在联欢会上表演了节目。
工会主席吴海元见我在看通告,热心介绍起联欢会上总额为50万元的抽奖——基本人人有奖;集团08年度的先进工作者——每人可得3000元奖金;员工每逢生日的福利——聚拢来摆一桌,切个大蛋糕,完了人手再提一个回家。记者看到,1、2月份沐浴到工会温暖的十多个人里,有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和名转张小飞。
傍晚开饭前稍闲,食堂师傅玩起了司诺克,车队师傅打两板乒乓,小卖部阿姨抽空上了趟厕所,洗衣房姑娘完成了一天的洗熨,关了灯将门带上。集团车队有20多台车,十几位司机,除了接送演员的班车、赵本山常坐的帝王,另有3台房车,一大两小,还有一台劳斯莱斯停在库房,只有贵宾来时才派用场。这些,放到沈阳市或者东三省的背景下,便也和谐起来——夜色下,悍马、英菲尼迪、宾利常跑在路上,不知车主是谁。
据崔凯介绍,如果不算本山艺术学院,赵本山的这个基地养活了300多人,包括演员和公司管理人员;如果算上学院和剧场的管理人员,大概近千人。
赵本山所到之处,工作人员那种肃然(譬如本来在说话的戛然而止),那种一律低眉顺眼迎候董事长的敬畏,让外人有些陌生;徒弟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啊”)见他犹如老鼠看见猫的描述,令人有些好奇;而关于这些年来他身边迎来送往,合久必分的传闻也颇神秘——这是那个背着山鸡和大蒜走进“苏格兰‘调情’”的农民大叔么?
那些70年代末、80年代初结识他的人,都深深记得他的谦虚、热情、淳朴、豪爽,今天也对“大腕”表示理解:“现在给人感觉挺高挺傲,其实,你说他处在这个位置上,不能跟很多人像过去那样做了。其实那样做更不利,脑子想事也不方便。”
辽宁省人艺的编导羊驰则这样分析:“霸气有两种,作为演员,如果不想站在舞台中央成为全台的灵魂,那他不是好演员。像我们老爷子(前院长)李默然,只要他一出来,往舞台一站,那种气场就会带动整个剧场,很多演员都会不自觉地跟着他走,观众的情绪也会被引着走。这就是功力,好演员都这样。生活中的霸气,就是不近人情了,则另当别论。”
结交30多年的崔凯说:“这是种管理方式。因为二人转演员都是社会人,很难管。人说你这些徒弟10个人能有12个心眼吧,他说能有120个,也就是说心眼特别活泛。他不霸道镇不住。”
分蛋糕
熟悉赵本山的人说,他的发展轨迹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合拍的,即所谓“寻找商机”、“做大做强”。不强大,就要受欺负,这个观念对中国人的冲击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58年《进化论》的发表。
赵本山的创业之路,与中国成百上千积累起可观财富的名人、非名人(至今表现为合法的那个队列)基本相似。只是他走得比较实,鲜有虚拟经济的成分:早年将铁法(铁岭法库的煤矿)的煤拉到本溪卖,后来筹办饮料厂没成功,入主辽足沾了一身“闹心”退出,最后锁定影视演艺行业,传闻中正在洽谈手机制造业……
他的产业链中目前最大的环节一是剧场演出,二是影视剧制作,二者呈连带关系。有受访者说,电视剧的定位和操作也体现了赵本山的经济头脑,“全是农村戏,演员都是自己旗下的艺人,外景地挪得离家乡越来越近,投入不会太多,没准别人还得给他钱。”植入式广告这个概念也不是赵本山的首创。
反过来,电视剧带动了刘老根大舞台的人气。用总裁刘双平的话说,这叫培养“粉丝”;用弟子刘小光的话说,这叫“银(人)熟是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沈阳的大部分剧场都被二人转表演占领,能演出别的艺术形式,如歌剧、芭蕾舞之类的场所大致只有3个:辽宁大剧院、中华剧场、南风国际俱乐部,后者也已被某企业承包。
沈阳市的二人转演出市场被业内评估为3个等级:一级是赵本山的3家刘老根大舞台;中档的有关东情二人转演艺广场、林越与梅成祥合伙经营的“群众电影院”二人转专场、位于梨园剧场的“盛京红磨坊”共3家;三级则由10家小剧场组成。
加上星罗棋布的夜总会、洗浴中心小舞台,据估算,沈阳市大约有100多处二人转演出场所,每天大概有一两千从业人员在演出。有的演员一晚上能跑9个场子。
至于外地的情况,崔凯说:“吉林有一个经营者给我看过一张北京的旅游图,他在上边插了小红旗,120多处,都是唱二人转的场所,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说大部分都是洗浴中心。我估计整个二人转的从业人员大概在10万人左右,包括演员、乐队、经营者,以及二人转光盘制作者、录音师之类。”
群众电影院90年代中就做得红红火火,背后两位都是二人转市场经营方面的前辈。林越的主场在吉林,几年前他旗下已有江城剧场、站前“艺吧”、临江大戏院3家演出场所,吉林市所有的二人转演出都由他安排演员,他还成立了关东林越艺术团。早在赵本山于沈阳成事之前,林越的二人转剧场已成为“吉林市的一道风景”,凡有大型会议、海内外旅游团去吉林,安排看二人转是必不可少的内容。2000年,赵本山就是在他那看了一场二人转表演后,决定回归。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1月21日正式开业的“盛京红磨坊”,出任总经理的是霍燃。霍燃的生意做得很大,就是制作和发行二人转光盘。因为年纪大一些的东北人还是愿意听唱段,他抢占了那块市场。东三省一批优秀的二人转演员,包括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韩子平、董玮、郑淑云、阎淑萍、董连海、阎学晶、杨金华,民间二人转著名演员王小宝、唐鉴军、张小飞、王小利、阎光明、王永惠、蔡维利、王金龙、张涛、孙晶、毛毛、司旭等,都在他那里录过光盘。而吉林二人转演员王魏三已出了VCD。霍燃的莎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沈阳最大的批发市场五爱街,面积有1000平方米,在全国各地还设有30多个销售网点。2002年底,他买断了赵本山投拍的电视剧《刘老根2》音像制品的东北地区总经销权;2003年4月,又发行了《刘老根大舞台开业庆典晚会》CD。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盛京红磨坊背后的大股东,其实是吉林名转魏三和孙小宝。
在东三省,长春市徐凯泉开办的和平大戏院也是二人转演出重镇。他背后有个名为艺委会的智囊团,聘请了省内文化界有威望、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核心人物宫庆山原是吉林省委宣传部某处的处长,“是个地地道道的文人”。
如此看来,赵本山的事业不孤独。这个江湖神龙出没,见首不见尾。赵本山起步稍晚,但他以老少皆知的全国影响力占据了一个至高点,成为当今二人转演艺市场的领军人物。
2001、2002两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奖赛”之后,林越旗下的张小飞、翟波、阎光明、王金龙等几个顶梁柱,相继离开林越艺术团,拜赵本山为师。一段时间里,林越的票房直线下滑。
演奏员出身的林越能创下一份家业,绝非等闲之辈。他平素低调、讲义气,颇有个人魅力,那些即使离开他的二人转演员都尊他一声“林哥”。他大方地说:他们能拜在赵本山的门下,作为老板我为他们高兴;只要他们有出息,艺术上能有更大的提高,我就是有再大的损失,也愿意为他们铺路搭桥。徐凯泉旗下的王小利有着非凡的嗓音,后来也正式拜赵本山为师。
江湖有道,有钱大家挣,何至于伤了和气。何况,吉林省有分布在长春、梅河口等地的十多家二人转大中专班,成为农村贫苦孩子奋斗的起点,“上辈子是裁缝”的二人转人才自会一茬茬长出来。
辽宁的二人转学校不如吉林多,一所在黑山,一所在新民。现在,又有了本山艺术学院。
赵本山也在构建他的理论,观众笑了乐了,就是硬道理。搭着时代的脉博,他提出的关键词是“快乐”、“笑”,它们频频从他徒弟口中流出,也融进台上演员的说口中:“观众要喜欢看,挺不住也得挺。”
一位沈阳朋友说,累了一天,不就想放松放松么。他外国女友就问:“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累?这是怎样的一天啊?”
师与徒
85岁的二人传专家王肯(一级作家,吉林省作家协会、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曾将跑江湖的二人转艺人比喻为“关东吉普赛”。唱屯场(村里)、唱木帮(伐木人聚居处)、唱棒槌营子(挖人参的地方)、唱子孙窑(有钱人家包场,或者几户人家合伙包场一起看)、唱大车店(赶车住店)、唱胡子窝(土匪窝),为了生存,哪一个民间艺人不练就一身察言观色、见人下话的本领?
74岁的马力(东三省公认的二人转舞蹈专家)则在家中为我们细述二人转的前世今生。说到兴头上,她拿出家什、连比划带舞回答我的问题:“什么叫手玉子?”“四角方巾怎么改的八角?”
二人转的技艺绝活、江湖道行就是这么一辈一辈往下传的。但琢磨了一辈子的玩艺岂能轻易传授。赵本山弟子中有“小才子”之称的蔡维利记得,70年代末他刚入前进艺术团,为了多学艺,常给老师打水,“可老师保守,一问就说没时间,不愿告诉。”他跑龙套,都是些大兵、打旗的小角色,只能在每次演出时偷着学艺。
记者采访时也问赵本山可曾拜过门,他说:“没有,生活就是我的老师。”盲二叔的二胡、笛子是他童年的“玩具”,扶着二叔走村串户的经历才是珍宝。
也是赵本山徒弟的王小虎记得,92年他最早拜父亲好友于小三为师时,提着一条烟、两瓶酒、两匣果子、两条鱼,当时叫“四彩礼”,进门就磕头,算拜了师。
身上很有些绝活的吉林人刘小光告诉记者,当时他已在别的剧场压了十年轴,很想拜赵本山为师,就托人打听是否要送些什么礼。后来他摸清师傅的路数:“我师傅不图这个,他爱才。”当他得知赵本山愿意收他后,拿着电话的手直哆嗦。他跟小沈阳同一批拜的师。
刘小光的才,在他演的赵四身上略有体现(当我们向赵本山夸他时,赵老师飞快地做了一个嘴角抽抽的动作)。10号晚看他跟妻子陈静一副架时,摄影记者叫好。他的双手黝黑,指节粗大,“种过地,出过大力”;问他过去,他眼一垂:“我都不愿去想。” 他曾被推荐给宁浩的《疯狂的赛车》,说好演男一号,到剧组又变了。他打电话给师傅:“让演警察了。可我长得像小偷,这能行吗?”师傅那边《乡村爱情2》正缺人,于是他回转来演了赵玉田的爹。
刘小光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能力和角度,是优秀的民间艺人所共有的。他给我们学浴池里一个年纪老大、动作迟缓的老头儿嫌池水上漂浮的那层埋汰,先是用嘴吹,后是用手推,然后又不好意思被人瞧见,缓慢地转头,四下望望,真是一出卓别林式的哑剧小品。
这些弟子,在拜师前已经有相当一段行走江湖的时间,也因为各有一手才纳入赵本山的视线。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拜师呢?小沈阳在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跟着师傅“不为挣钱”;蔡小楼说,“没有赵老师二人转早就被踩平了。像我这样一个唱二人转的民间艺人,能唱到省一级的文艺团体,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刘小光说,跟了师傅以后,做人方方面面有改变,师傅教训“台上做戏台下做人”,走道也不兴摇头尾巴晃了。
这些弟子,多是家境贫寒的农民的孩子。他们在该下地的年龄没能热爱上种地——小沈阳的母亲说,小沈阳七八岁、十来岁时一下农田就看父亲的表,盼望早点结束。有一位年龄稍长的出租车司机根据他听来的传闻,向我们数落赵本山当年“不好好干活”的事迹。记者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位民间小说家的报道,也提到乡人眼里他“不安分”的种种表现。
赵本山不止一次向媒体说,年轻的时候就想离开农村,想出去,因为农村太苦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他第一次在铁岭的家里安上座便器、铺上地毯,乡亲们来了仍然蹲着拉,弄得到处都是,还往他的地毯上吐痰——即便如此,他是高兴的。因为他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他的徒弟们,也各有辛酸的第一步。小沈阳是父亲背着他走出10里地,揣着借来的700元去考铁岭的艺术团。学费要1000。他唱了两句,团长说,留下吧,学费先欠着。这300元一直欠到今天。如今小沈阳衣锦还乡,喝点酒还会落泪:“妈,咱家那时候咋就那么穷呐?”
孙丽容回忆第一次跟着小班十里八村走着演的情形:“家里那时真是穷得一点钱也没有,妈为了给我置办演出服,卖了20只母鸡。我揣着20只母鸡换来的27元5角,手里拿着一张地图,到沈阳中街买了一套化妆品,一套绿衣红裤。”
为了生存,蔡维利有段时间抬过木头,堆过坯子。所以2002年11月15日拜师那天,他给师傅磕头时发出“咣当”一声响,一层楼都能听见。他端着酒杯含着眼泪对赵本山说:“师傅放心,我绝不给您丢脸,今生今世一定好好孝敬您!”
王小虎最早跟的是鼓乐班,给人办丧事时叫他去唱戏。他拜门时磕了无数个头,一边磕头一边眼泪刷刷地流,当时在场的人都哭了。“当天晚上我一宿没睡,之后好几天都没觉,饭也吃不下去,就是高兴。总合计是在做梦吧?祖坟冒青烟了?我给父母打电话报喜,他们都乐坏了。”
有多少城市人能理解小沈阳父亲在09年正月里,对着驱车5小时赶到他家的记者们说出的那句致赵本山的话?——“大恩不言谢,给师傅增光添翠!”
不过是想过上好日子,却一步一步卷进一个充满名利诱惑、真情与虚伪交织、强凌弱、弱倾轧更弱的江湖,想要保持清醒或置身事外,也难。这不仅仅是二人转的江湖,也是中国社会当下的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本”色
许多人成名之后掩饰或避谈自己不高贵的出身,赵本山偏不。他大大方方说自己是农民,有时还故意稍稍放大。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大手笔的幽默感常常胜任生活中的佐料、润滑剂以及某种武器。
记者在采访中听了不少段子,譬如他对带“长”字的官员开玩笑:“嚯,黑社会来了。”正当众人怔住、空气凝固之际,他转身就甩个小包袱:“哦不是,我是说社会黑。”
采访中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中国农民是最聪明的。中国人所有的智慧都在农民身上。就像那些乡村系列剧中讲述的那样——农民那种张家长、李家短的勾心斗角,那种为了一亩三分地、鸡鸭鹅狗、油盐酱醋的计较和算计,那种把浑身智慧激发起来的忙碌——农民就是那样的,又淳朴善良、又聪明狡黠。”
也有人认为,与其揣测这是赵本山的高明,不如相信人尚存天性。
“他一找不着感觉就回农村,回他那个莲花乡,跟老百姓坐在炕上吃点水豆腐,唠唠家常,看看他们生活的艰辛,他说我就找到感觉了。有时候唠嗑,他说他做梦也没梦着有今天。他对人世看得很明白,头脑也很清醒。有时我说,你这名起得好,占个“本”字,没忘根本。”崔凯说。
“但这几天我们能近距离看到他,发现他一身名牌,低调的奢华。”有记者说。
“还行吧。包括我们在剧组吃点东西,他也不摆谱。好日子他能过,回到他那个村里和老百姓还照样。有次回去走到老百姓家,他说我饿了。那人说你谁啊。他说,我是赵本山啊,你们家有大酱没啊。后来装了两罐大酱回来,把他高兴得够呛。”
“听说他对家乡人挺好,属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那种。”
“赵本山在他没多少钱时就给乡里建了一所希望小学,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他还没在全国出名,刚有‘希望工程’的时候,团省委找我问问赵本山能捐点钱不,他说行啊,这事能干,就捐了个希望小学。那天赵本山去剪彩,校长抱了只山鸡站那儿致词,说山鸡也能变凤凰。这次汶川地震,还没人发动,他先捐了100万。后来到了央视,他在那儿合计了半个小时我该捐多少呢?捐多了别人不好办,捐少了心里不落忍。我说中央台已经捐了的是多少,他说有捐10万,有捐20万的。我说你捐100万大家都知道了,就再捐个10万、20万吧。他说那不行,我不能超别人太多,但怎么地我也要拿100万,就又捐了100万。这么多年,他善良的心地没有变。”
(鸣谢李微《东北二人转史》、王肯《二人转史料》、霍长和、金芳《二人转档案》,对采访提供帮助的芦哲峰先生,以及整理了大量录音的实习生李少卿。)
《南方人物周刊》:生于江湖,但不能死于庙堂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
东北老百姓说,那三宝跟咱普通人关系不大,生活中咱主要靠另外三宝:大米饭、止痛片、二人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东北”就是以山海关为界的东北部地区,从行政区域上来说,它主要指的是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咱们疙瘩都是东北‘银儿’”,东北“银儿”其实是当年去关外的汉民(尤以山东人为主)和关外的原住民(满族、高句丽族等等),经过100多年通婚融合,形成的新种群。从人多地少、十年九旱的山东地区迁徙至此的百姓,发现这里“棒打狍子瓢舀鱼”,只要肯下力气开荒,土地到处不缺,就住下再也不回去了。
一亿零三百万东北人,撒在7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置身地广人稀的极北苦寒之地,他们养就了独特的性格。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东北啥环境?冬季非常长,哗哗大风大雪,所以得大块吃肉,大口喝酒,都喝白的,因为冷啊!大高粱烧子,哗哗来几口,就出汗咧!东北人为啥说话都声大咧?离得远!现在逐渐繁华了,以前东北一堡子跟一堡子之间距离非常远,所以扯开嗓子:‘哎——干啥去?’包括女的说话都老高了:‘哎——咋地!’跟呼嚎干架似的,其实根本不是干架,她就是那种性格儿!”
猫冬猫出的二人转
李青山是全东北有名的老辈二人转演员,他拜师的故事在二人转演员中口耳相传:李青山原本是个放猪娃,被唱戏的老艺人相中了,说这小孩儿嗓子挺不错。结果他妈妈、奶奶都不同意他去学二人转,李青山就偷着跑了,到东三里去撵那伙艺人。到那屯子一问,说“二人转在哪唱捏”?“在前院唱呢。”李青山掉脸就往前院奔,走了60里地,才走到了前院。
那会儿的东三里,家家户户不锁门。据李青山说,东北人热情好客,随便到了谁家,主人不在家,自己就可以进屋做饭吃,吃完把碗一涮,出门在地上划个十字,你要是往南去了,就把南边那一竖划得长一点。主人来家一看就知道:来客现在往南去了。
国家自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席专家、辽宁大学教授巫丙安还记得小时候村里请二人转唱堂会的盛况:“刚化着妆的时候我们就跑去看,南炕北炕都站满了,窗户上都是人,根本挤不进去,怎么办?有的人就趴在房顶上,用脑袋从窗户眼望里看。如果这一个礼拜6、7天在我们家唱,那这一个村子什么活儿都不干了,着火了都没人管!”
曾经跟拍过有关东北二人转记录片的温普林说,东北人好逗笑,可能跟那里气候冷、人稀少、生活枯燥有关系。“一年里有半年是冬天,外面天寒地冻,啥事也干不了,只能在家呆着,他们叫‘猫冬’。”
要叫二人转,不要叫蹦蹦
二人转起于何时,兴于何处,源于何种曲艺形式,不同的学者、民间艺人、考据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这种艺术形式是在嘉庆年间,脱胎于东北大秧歌,借鉴吸纳了莲花落、什不闲、东北大鼓等不同的曲艺门类,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迄今已经有了近300年的历史。
东北大秧歌是民间文化的早生子,在元朝之后,农民逢年过节就自发地组织起来走村串户去表演秧歌。秧歌舞的队型是排成两行,一边是男,一边是女,那时候女人不能抛头露面地跳舞演出,所以都是由男人抹上脂粉穿上花衣假扮的。秧歌以“女”为主,旁边的男人绕着旦角舞,一会去逗一下,表演动作里就逐渐有了动手动脚,甚至一些男女调情的说口。
白天看秧歌不满足,晚上,农民们就把唱得最好、长得最美的那一对秧歌队员请到屋里去了。
“东北那种南北大炕,一大家子,包括老公公、新媳妇,全在一个炕上暖着,剩下的也就是三四尺宽的地”,秧歌根本舞不起来,艺人没办法,只好在说唱上下功夫。点上一盏油灯,唱个《白蛇传》、《绣荷包》啥的,大多是江南、河北、山东等地的民歌小故事,用东北的曲调来演唱。这就是二人转的雏形。
春天铲地播种毕,东北叫“挂锄”,得唱20天二人转;秋收完了,再唱半个月或20天,一年这两季几乎是二人转的季节。到了猫冬的时候,二人转就更加必不可少。春秋两季的二人转,大多在场院里,露天里唱,所以有个别号叫“滚地包”;田间垄头、粪堆之上表演的,叫“滚土包”;天寒地冻在屋里炕边上唱的,叫“靠炕沿”。
唱丑的看相,包头的看浪(‘包头’指装扮好了的女角)。屋里简陋的灯光就谈不上啥舞台照明了,丑角举着油灯、围着旦角唱做,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四周的观众都能看清旦角的俏脸。他们因此练就了一手绝活:随便怎么转,灯花不兴有一丝跳动,更不兴有灯油溅出。
《陪都纪略》里已经有二人转的记载,在当时的十多种曲艺形式里,二人转还没有今天这个学名,它的土名,叫“蹦蹦”。
“民间都叫‘蹦蹦’,到后来还这么叫。艺人不愿意,兔子才蹦呢。他们愿意叫‘莲花落(音同‘烙’)’,还专门编了一段‘说口’:‘要叫莲花落,喜事就来到,出门卡砖头,元宝望家抱。谁要叫蹦蹦,扭头就败兴,出门卡跟头,回家就得病。’”
1930年代大连的《泰中日报》上已经用到“二人转”这个词,真正定下来,是1952年12月,原辽东省搞文联艺术汇演,艺人们提出来,“蹦蹦”这个名字不好,讨论了3天,最后提出了“二人转”的名字。
漂流行多苦也得逗别人乐
闯关东的人生活艰苦,所以渴求欢乐。在田间地头,他得说说笑话,说说歇后语,要逗一逗,甚至乐于自嘲,这就是对劳作生活的一种放松和解脱。
“他终于在他生活的经验里面,用他的理性找到一个规律:越穷越有盼头。今年盼不来咱盼明年,这辈子盼不来咱盼下辈子。老有这么一种盼头在。想通过这种文化生活创造出一种喜剧人生,用这种喜剧人生,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巫丙安说。
人们看二人转,目的很明确,主要是找乐。就连悲剧,都得悲剧喜唱,不能够一悲到底。
民国时期出现过一段二人转,讲的是3年饥荒,冯魁一家为了不让孩子们都饿死,打算把孩子卖掉一个。卖男孩吧,就叫老冯家断了香火;可是卖女孩吧又卖不出价钱,救不活一家人的命,于是母亲挺身而出:“卖我吧。你们在家好好过日子。”
这是一个非常悲苦的戏,唱的时候艺人们都得掉眼泪,特别是在临别一场戏,为娘的就叮嘱:咱家还有半碗小米,藏在什么什么地方;还有几枚小钱,将来怎么怎么用;还有一捆柴火……买妻子的是个做小买卖的,赚了点钱,说赶上荒年买个老婆过日子吧,结果夫妻告别的时候,把买主感动得哇哇大哭:不行了!把钱也给他们家了,老婆也不买了。
“是个大团圆结局。那个时候,冰天雪地,军阀混战,豺狼虎豹,人民生活已经很疾苦,在艺术里再表现疾苦,那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所以二人转千方百计地要提供一些欢乐,一些希望,给人信心。”“只要小手帕一转,小唢呐一吹,人身上的律动就是生机勃勃的,而不是大悲大痛的,灰色低调的。你家里有多悲多苦的事儿,只要一听了这个小唢呐,就不一样了。”
在旧社会,二人转演员社会地位很低,属于下九流,正经人不屑为之,只有那些家境贫寒又痴迷曲艺的才会入了这一行当。“出来献艺,一走大半年,到春节总得回家吧?天不黑都不敢回家。等着天黑了,溜墙根,偷偷回去,就怕给人瞧见。”二人转老演员安志斌说。
三教九流里:“七娼八浪九吹手,”演戏的属“浪”,是“漂流行”。“管妓女还得叫姨呢,小一辈儿,人家是坐娼,你唱戏的是走娼,唱二人转多大的腕儿,见了妓女都得叫姨,就不拿你当人看。”
给地主富人家唱过堂会的二人转演员,都有过唱通宵的经历,一宿一宿唱,唱到第二天日出,老有人点,就老得唱,小鸡开口了,艺人才能闭口。喊累?不行!有时候实在唱不动了,那些大老爷们就会给艺人一些大烟点上,强制兴奋了,再唱!
保护二人转,就像保护地下党
从清朝到民国,再到伪满,几乎历朝官府都禁止过表演二人转,理由无非是伤风败俗。这种民间土生土长的文艺形式里,多少携带着粗野泼辣的基因。
“场院里唱,宅门里唱,一唱到后半夜,就把看的孩子呀妇女呀都撵走了,剩下的都是男性观众,这时候就要求他们来点荤的、粉的。点名要这些。演员都是男的,观众都是男的,就像现在讲讲荤笑话似的,各种荤段子荤说口就来了。”
在行话里面,二人转又叫“谣”,艺人们把家庭演出叫“子孙谣”,兵营里演出叫“翅子谣”,大车店里演出叫“轮子谣”。对子孙谣有严格的限制:不许卖笑,不许卖肉,不许说脏口,不许说粉词儿。轮子谣和翅子谣面对的观众都是小伙子、当兵的、老爷们,就可以说得放开一点儿。
“东北闯关东的光棍比较多,有性饥渴,所以艺人说说黄色的、淫秽的,释放释放。艺人们是什么地方什么唱法,什么对象什么唱法。比如《西厢记》里有一段《荼蘼架下》,莺莺和张生在荼蘼架下野合,艺人一看,今天来的正经人多呀,他就掐了。一看今天是在大车店,他还临场发挥了。所以聪明不过艺人,伶俐不过江湖。”原长春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兆一说。
何庆魁(已故笑星高秀敏的丈夫)说,“张作霖就不许演二人转,连他家人都不许看二人转,有一次他出远门,家里就请了一伙二人转班,在家里围着偷偷地唱戏,正唱着,大帅回来了。家里人吓得不得了,这得惹多大的祸呀?二人转艺人一看张作霖回来了,马上就现改词,改说口,说的是张大帅怎么怎么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救了关东救了中国,尽歌功颂德,把张作霖说笑了,从此以后他就不管了。”
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性教育的传统,在过去的东北,老百姓最普遍的性教育手段是听房:哥哥结婚了,家长鼓励弟弟去听。二人转里那些或暗示或赤裸裸的性内容,也成为了另一种性教育的补充。
1931年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给老百姓都发国民证,惟独不发给艺人,不承认他们是国民。那时候的二人转演员,只有极少数还敢窜上街头演一演,还有些艺人就直接参加抗联了。
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也没把二人转的火星掐灭,二人转走进了深山老林,甚至有人专唱反满抗日的段子,他们给矿工唱,给渔民唱,给采人参的和采蘑菇的唱。夜深人静,把窗子挡严,外面再布两个放哨的,小锣小鼓就开张了。
“有的村民白天把艺人藏在菜窖里,躲起来,锁起来,晚上出来唱,对二人转艺人的保护,就跟保护地下工作者似的。所以日本人也没能把二人转赶尽杀绝过。”
为人民服务不能撒春
二人转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进城。
传统二人转精粗美丑不分,国家干部就去宣传政策,今后就这种演法恐怕不行。”解放初期沈阳有13个二人转班组,成立了沈阳蹦蹦戏改进协会。
说口不让说了,脏的、粉的不让说了,封建迷信也不让演了。
肯定与纠正,恢复与发展,加上新文艺工作者的介入,二人转就这样携带着生命力曲折前进。有人依然爱它,有人持续鄙视它,但是谁也不能忽视他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变通能力。
二人转在形式上比说书、唱戏都更灵活,说大点是为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说小点为了自己吃饭,他们会想出各种方法来适应它的发展,从来不敢得罪观众。政治热点,流行歌曲,手机短信,网络笑话,当时有什么他们就演什么,唱的说的都是社会上最流行的东西,听起来很有时代感。
凡是民间的东西,往往生于草莽,兴于江湖,死于庙堂或殿堂。民间艺术一旦走到宫廷,走到极致,往往也就意味着它快走到终点了。俗很活跃,但是粗野,雅很高贵,但是和寡,在俗和雅之间,二人转还在摸索平衡点走钢丝。
(感谢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制片人陈晓卿;感谢段锦川的记录片《二人转:一百年的笑声》;感谢艺术家温普林拍摄的大量记录片素材对本文的帮助。)
不许丢单;不许拉烟;不许错报家门;不许误场;不许滥唱;不许犯狯(意即:不许说不正当的话);不许吵谣(不许在某处住下后乱吵乱闹);不许抠斗挖相(不取外行的钱物,不占内行的便宜);不许招邪(不许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不滥道。
——这是二人转的十条行规,人在江湖,得遵守江湖人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