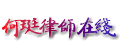政治报刊的中国式生存
2274 人阅读 日期:2008-06-04 21:43:27 作者/来源:田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会成了中国新闻界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走秀场,不仅各地党报、卫视要派一大群记者跟着本地官员进京,报道他们的一言一行,商业网站的编辑们也在想方设法把散会后的官员们拉到直播间做访谈,还有一些周报、月刊,总要挖空心思从委员、代表们一些怪诞的建议和言论中榨取些看似严肃、关涉国家前途命运的话题用来做封面报道。
把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放在媒体的闪光灯下,把人民大会堂里召开的会议的细节通过各种形式传递到全国各地,无论如何这似乎都是中国传媒和中国政治的双重进步,中国政治的内涵虽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是,形式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比如,各种各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尽管这意味着政治家们在操纵他们的公共图景时变得日益老练,但它仍然使得政治较之以前更为开放和更易接近。不管有多少限制,这毕竟是我们最能接近中国政治原貌的一个途径。连采访两会的德国记者也会感慨“中国政治变得有趣了”。
但是,那些以政治为业的中国传媒更加幸福了吗?中国的时政记者们做得比以前更加出色了吗?衡量这个问题,遥远的例子有美国的李普曼,还有中国的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近的则有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社里那一大批家国天下、快意评弹的时政记者。只有在新闻系的资料室里翻阅那个年代的报纸时,我们才会感慨,目前这一代以政治写作为业的记者们做得有多差。
无奈的批评者
在公共生活的条件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对通过媒体展示的可见性和自我呈现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一项必备的和日益专业化的特征。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应该对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美国,1969年,总统尼克松创立了白宫通讯办公室,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任务是,不仅要控制行政官员说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公共场合露面,还要尽可能地影响媒体都说些什么,以保证行政部门能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策略则更具中国特色。对于政治事件的报道权利,事实上依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严格意义上的官方传媒机构所垄断,对于这些机构的控制显然比那些追求发行量、广告量,以商业目标为第一追求的传媒机构容易得多。
所以,一直以来,政治报道中真正优秀的作品,仍然只能出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记者之手,只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这样的作品,已经变得越来越罕见。这不是因为政府的控制比以前更加严厉了,而是中国的传媒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记者都流向了那些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义的媒体机构,在他们的努力下,那些媒体越来越被称为真正的主流,开始掌握实际的舆论控制权。
近几年来,市场化的媒体度过草莽时代之后,都在竭力追求转型,希望脱离原本赖以成长的草根形象。而要变得主流起来,这些媒体的领导者们几乎都把加重时政报道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转型的最佳途径,但这远远不像当年依靠底层社会写作那样顺风顺水。迄今为止,在市场化的媒体上,直接把政治事件作为报道主体的新闻作品中,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之类媒体相比,仍然价值不大,或者说仅仅具备写作意义上的价值。
最有价值的政治报道,是那些能在第一时间将最核心的公共决策传递给读者的新闻作品。在现有的体制下,以政治信息提供为主要诉求的新闻报道,将会继续被新华社等机构所垄断。除此之外的那一大批时政类报刊上所刊登的所谓时政报道,大多是针对公共政策的评价、激辩类文章,对于一个新闻机构来说,这只能是次优选择。无数的事实证明,这一类文章,要想取得中国读者好评,一个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对于政府的大部分行政决策,都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观之。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论杂志《观察》,其总编辑储安平后来在领导《光明日报》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媒体只需批评就行了,至于怎么做,应该由当政者去想。他短暂的《光明日报》生涯也践行了此说法,并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对于今天的政治刊物来说,这个做法更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当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刻,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出台,只要用不同的价值观去衡量,总会找到一连串批评的理由。
笔者曾经写过一组关于中国铁路改革困境的文章,对于这两年来铁道部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如以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来衡量,铁道部的行为有着诸多可抨击之处,但其实,若以效率、发展的价值观来衡量,则铁道部实在是为中国改革做了相当大的贡献,其种种政策即使造成了不当后果,也多有可谅解之处。
对于关注中国政治的公众,和喜读政治刊物的读者来说,最理想的传媒生态是,以不同的价值观写作来进行身份识别,而不是以官方和市场来区别,对于每项公共政策,不同的评判在不同的价值观媒体上激烈交锋。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优秀的时政记者和报刊,无一不是具有坚定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的人和机构。可现在,这样的理想状态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市场化的媒体,同样都没有坚定的价值观,前者唯领导者意志是图,后者唯利是图。
双重困境
在西方新闻学的研究议程中,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演进被无数的研究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过梳理和剖析。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将独立的出版社视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成分。他们将观点通过独立的出版机构的自由表达,看作是对于腐败或者残暴的政府滥用国家权力的最好的抑制手段,认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出版社,会起到批评性的监督人的作用,它将详细审查和批评那些统治者的行动。
但是,随着现代传媒飞速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以来,面对媒体机构普遍的企业化,媒体产品的商业化,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对媒体影响政治的正面效应,越来越持不太乐观的态度,媒体的早期批评家中,马克斯·霍克海默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把媒体称为“文化工业”,认为这将导致压迫性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简单地说,商品化了的媒体产品,无法再承担起新闻学这个学科创立之初所设想的崇高理想。
现在的中国传媒,面临的则是双重的困境,他们无法承担起抑制政府滥用国家权力的责任,更无法避免商业化和工业化的侵蚀。21世纪前后10年内,中国也曾涌现出了一大批依靠揭露社会问题,获取道德优越感,从而迅速取得成功的媒体。身处广州的《南方周末》和《南风窗》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他们只是因为敢说,就被公众拔高到一个社会良心、道德符号的高度。长久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用理想化的符号来代替现实的存在。
那个年代,两份报刊的责任感和纯粹的品格都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跟读者的关系,是向导者和支持者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不仅成就了两个传媒机构曾经的辉煌,甚至一直让他们受益到现在。可是,这样的关系如此脆弱,在经济型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席卷了一切领域,就连生产精神产品的媒体同样如此,在这样的现实里,向导者和支持者的关系还能有一席之地吗?
如今,中国的政治思想类刊物,或者说还具有论政热情的报纸和杂志,保存的还有两种,一种是诸如《炎黄春秋》之类的小众刊物以及网络上的一些小众论坛,保持着纯粹的品格,他们的领导者和编辑们没有蓬勃的商业理想,秉承着同人刊物的理念和气质,他们的言论更加真诚,但是,他们无法也没有热情去接触中国政治日常运作的现实并因此而缺乏力量。而另外的那些在商业理想和政治理想夹缝中徘徊的报刊,则在转型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四不像”。
更大的疑问还在于,人们还关心政治吗?尤其是中国政治,真得能像那些媒体的领导者预期的那样有足够的“卖点”吗?用“政治”的路数来挣“经济”的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还是纸上谈兵?
当年在封面上印上《朱基:把心交给中国》这样的题目,就可以洛阳纸贵,而如今,为了规避“新闻纪律”带来的风险,能刊登出来的政治报道,要么写得平淡,要么就是用理论化、技术化的文字来处理,这样做的结果,通过了宣传部门的审查,也失去了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
还有那些真正优秀的、有志于政治写作的记者,在市场化的媒体机构里越来越无法获取上升的空间和写出优秀作品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期望并想办法进入传统的官方传媒机构,获取官方身份意味着获得更多近距离接触中国政治操作内幕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困境,都让人对中国能否出现成熟而出色的政治传媒不能持乐观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些困境,让中国的政治传媒有着足够的上升空间,他们的进步与倒退将会与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保持大抵一致。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