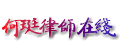中共地下党员刘敬坤:若无花园口决堤中国将亡国
8075 人阅读 日期:2012-09-29 16:58:55 作者/来源: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那没办法,战时没办法,他如果不把黄河决口,不把那个14师团消灭掉,14师团如果攻下来以后没有人敌得住。它有两万多人呢。
解说:抗日战争初期,上千万的中国人历经千里的颠沛流离奔赴大后方,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凝结着一部国破家亡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讲述者刘敬坤先生既是这场大迁徙的亲历者,也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今年82岁的刘敬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离休干部、民国史专家,他不仅著书立说,在20世纪90年代还曾经参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翻译工作。当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老人已经为了这部书的再版进行了9个月的推敲和修订的工作。
刘敬坤年近七十才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年过八十还在对手中的大部头进行修订,他把这些归功于良好的中学教育。然而他的中学时代却是在战火和动荡中度过的。
刘敬坤是安徽人,出生在阜阳南边一个名叫霍邱的地方。1937年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刘敬坤看见学校里来了一位军人。
刘敬坤:东北军的一个军长,因为抗战从西安那边调来,就住在我念书的小学里边。后来上海撤退的时候,这个军长在松江阻击,日本飞机来轰炸,他就炸死了。
解说:这个军长叫吴克人,是东北军第57军军长。他是刘敬坤抗战时见到的第一位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他牺牲在异常惨烈的淞沪会战当中。
刘敬坤:1937年11月13号上海沦陷,12月13号南京沦陷,这一个月的时间,第一线兵力在上海总共伤亡了30万人,整编的那些精锐军队全部伤亡了。上海撤退真是溃不成军,但是有一个特点,把它战争的重心从北方引到上海来了,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日本一直从北向南攻,那对中国很不利,因为河北、河南这都是大平原,日本机械化部队很有利作战的,引到上海以后都是一些沼泽地带,它就不利于作战了。
特别是南京失守,南京大屠杀以后,就感觉到亡国问题了。我那个时候上的是私立中学,这个校长是同盟会的,南京是12月13号失守的,12月14号早上升旗的时候他痛哭流涕,说我们对不起先总理,我们让先总理蒙难,南京失守了。那个时候南京失守对人心的刺激是非常大的。
解说:日军抽调重兵大举进攻徐州的时候,刘敬坤正在安徽省立颍州中学初中部读书。1938年4月,在徐州会战中,李宗仁组织指挥了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全面抗战的第一个大胜利。川军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滕县保卫战,死守孤城的就是川军。但是台儿庄大捷之后,日军反而加紧了对徐州的包围,1938年5月,刘敬坤在学校里得知了徐州失守的消息。
刘敬坤:李宗仁从徐州突围出来了,就在阜阳指挥大军撤退,我们那个私立中学校长就去见他,李宗仁就说你们搬到河南潢川去。当天那个校长吃饭的时候就讲明天3点钟起床,4点钟就要出发,一点都没准备。
解说:1938年徐州沦陷之后,5月24日刘敬坤和老师同学们一起离开学校所在地安徽阜阳,踏上了内迁的路途。
早在1937年秋天的淞沪会战期间,148家民营工厂就已经迁出了上海,而1937年10月上旬,南京中央大学成为第一个进行内迁的高等学府,拉开了高校内迁的序幕,此后工厂、学校、政府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普通难民纷纷向西南的大后方迁徙。在刘敬坤看来,抗战期间全民性的内迁,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之下一个必然的选择。
刘敬坤:沿海必定要沦陷,因为这个大平原完全适用于日本机械化作战。抗战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一定要从东部转移到西南去,抗战前,这个蒋百里——蒋百里是钱学森的岳父,是个大军事学家——讲,中日必将一战,将来我们一定在三阳以西来抵御,来决战。三阳是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以西,基本上抗战的形势就是这样的。所以抗战整个的形势是要从沿海向西部进发,迁移到西部山区,实际上迁移到西部山区等于是国家的重建。
解说:1938年5月24日,15岁的刘敬坤告别了家乡,跟随学校踏上了迁往大后方的路途。
刘敬坤:24号早晨我们吃过早饭了以后,教国文的陈先生说我给你上最后的一课了吧,他讲啊讲啊,就讲陆游的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陈先生给我们念这首诗,这个先生是进步的,后来也没有下落了。
3点钟起来以后,4点钟出来,走在小路上听到有个人唱“我的家……”,就听,听了以后也就跟着唱,后来一唱,哎哟,唱不动,就哭,都哭得不能走路。
解说:出发当天,刘敬坤和堂兄一起多走了30里路回家与亲人道别。没有想到,从此一别8年。
刘敬坤:我这个堂哥的母亲,还有我祖父,坚决不准我们去,说要死死到一块。我父亲讲:死到一块?留两个根不好吗?我父亲给我讲了一夜的话,我就听了两句:能念书就念书,不能念书就到军队里拿枪跟日本人拼了吧。
解说:1938年六月初刘敬坤到了河南潢川,当时潢川正是大军云集,南北城全是从徐州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军人。可是,学校在这里却不能长久地停留。
刘敬坤:到了潢川以后,广西桂系军队想把我们编到他的军队里去,结果我们这个校长(我没接触,我猜)就发电报到武汉教育部,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就派邵华和方治到安徽,他名义上讲去看安徽的学校的情况。他也是安徽人,就是那个国民党监察委员邵华,他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后来当过国立第8中学校长。我还记得邵华到潢川给我们讲话,说“你们都是不足三尺的童子”,他手还比划,“怎么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到后方念书去”。
解说:刘敬坤记得,是这个邵华动员学生们迁移到武汉继续求学,几年之后,也是这个邵华,作为中学的校长剥夺了刘敬坤在后方继续求学的权利。
1938年6月初,刘敬坤和同学一起从河南潢川向湖北武汉进发。这一路上,越来越多的来自沦陷区的难民汇成了迁徙的人潮。
刘敬坤:我们就是跟难民一起走,晚上睡的时候有时候跟难民住在一起。
解说: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当时难民迁移的画面。在每个难民的胸口有一个小小的白布条,这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给难民去往大后方的“通行证”。
刘敬坤:只要你自己愿意走,到后方去,你到乡政府里去讲,我几个人,哪一天走,他就给你一个难民条子,白布的,上面写着名字,从那一天起就发给你一天两毛钱,规定你一天走60里路,5天到哪一个难民站,那时山里有难民站的,他到那凭这个条子,再发给你一个人一块钱,你几个人,他就给你几块钱,就那样一直到武汉。这是政府组织的。
解说:1938年6月中旬刘敬坤到了武汉。在当天的报上他看到这样一个消息,不久之前的6月9日花园口决堤,报上说洪水泛滥是由于日军飞机的轰炸所导致的。但事实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在徐州失守之后阻止日军精锐部队14师团进攻武汉,决定“以水代兵”,自掘堤坝,花园口决堤之后洪水一泻而下,日军第14师团和16师团大部被黄河水围困。6月28日日军撤销归德战斗司令部,第二天日军在徐州开联合追悼会哀悼战死者7452人。从此,日军沿平汉线南下的计划的确是被粉碎了,日军不得不改变计划,将主力南调,配合海军沿长江西进,进攻武汉。但是另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花园口决堤造成的中国受灾人口达到1000多万,300多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失去了生命。这个胜利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刘:那没办法,战时没办法,他如果不把黄河决口,不把那个14师团消灭掉,14师团如果攻下来以后没有人敌得住。它有两万多人呢。
解说:1938年6月中旬,刘敬坤和同学们一起从河南潢川步行到达了武汉。一首《保卫大武汉》的抗战歌曲其实就是刘敬坤到达武汉的时候学会的。那时候的武汉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的所在地,同时也云集了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流亡学生。武汉一度成为抗战的临时首都,这让当时只有15岁的刘敬坤印象格外深刻:那时汉口的所有学校都改作了难民的收容所,刘敬坤也和难民一起住在位于武昌的一所中学里。对他而言,当时武汉的一切都显得很新鲜。
刘敬坤:在武汉,我们那一天到南湖飞机场,顺着铁路走,看了很多苏联飞机,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叫苏联飞机,就叫俄国飞机,它那个航空服背上写着“洋人来华助战,军民一体保护”,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解说:1938年7月,武汉举行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纪念大会,刘敬坤至今记得在中山公园看到的人们为抗日献金的情景。
刘敬坤:大概是个华侨,他拎个包,大概装的是钞票,很大的一个包。他说我来捐献,把他西服脱下来也捐献,后来钢笔、手表全都捐献了。我亲自看到了讨饭的献金,拉黄包车的献金,还有妓女献金——妓女,确确实实的,我们当时在汉口看到的。那个讨饭的讲,我是讨饭的,我今天就献金,我为国家来献金,他说你不相信,你可以看。那确实很感动人。
解说:当时在武汉发起救亡活动的除了国民政府,还有各民主党派,共产党人周恩来等也在武汉。刘敬坤发现有几个自己的同学背起行囊离开了学校,他慢慢知道他们是“投共”去了。
1938年8月初武汉开始大疏散,刘敬坤所在的学校已经改为国立安徽中学,学生们被小船首先运到了武昌的金口,准备从那里向湘西进发。
刘敬坤:我们船到金口的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扔的那个炸弹把水炸得这么高,机关枪在打,军舰不让我们船靠。我们船也不管让不让,我们就要靠,靠到一个兵舰旁边,跟前大概离得还有这么远,大家都朝那个兵舰上跳,从那边可以上岸。我也跳了,因为小,身上还背了个行李,一跳,脚踩到兵舰旁边那个地方,就马上掉下去了,当时我们每一个人跳下去时都有一个海军站在那里,那个海军士兵就抓着我这个胳膊一甩,把我甩到兵舰那边,甩到地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帽子上面写着“中华民国中山舰”,我觉得如果不是那个水兵把我一甩,掉到江里去就没命了。
解说:两个月后,这艘著名的军舰在武昌金口江面被日本敌机炸沉,全舰官兵壮烈殉国。刘敬坤当时已经离开了金口,他和同学坐在一艘运煤船的煤堆上,沿着长江前进。
刘敬坤:日本人的飞机在上面轰。我在嘉鱼县这个地方(现在叫做赤壁了,这个县靠在长江边),一个轮船半个跑到上面去了,就剩半个,炸了,那半截大概炸沉到江里去了。这是亲眼看着的,我们坐着小木船逃跑,飞机在我们头上转,光转,也没打枪,大概看到不值得轰炸,所以我们幸免于难。
解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军事、教育和文化中心成功地实现了向西南地区的转移。刘敬坤觉得,这正是国民政府组织武汉保卫战的目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军队付出了自侵略中国以来最大的军事代价,得到的只有一座空城。而此时,刘敬坤已经和同学们在湘西正常上课了。
1938年9月下旬,刘敬坤和学校的师生们一起辗转到达了湖南的永绥地区。
刘敬坤:西南的落后你真的想不到。我们到了湖南花垣,那时候叫永绥,一个县城里面没有饭馆,没有一个百货店,那里的人称抗战为国仗——打国仗了,天上飞机叫洋雀,地上跑的车叫洋马。那都是西南人。不是经过的根本想不到。
解说:就在如此落后的西南,国民政府设立了22所国立中学。刘敬坤的学校因为是第八个到达西南的中学,在西迁后改名为国立第八中学。
刘敬坤:我们这个国立第八中学规模最大,有11个分校,等于一个省的教育了。上学全公费,还发衣服、棉被。
解说:刘敬坤说,在抗战的八年中他一无所有,穿着草鞋,衣衫破旧,但是他却受到了非常好的中等教育。
刘敬坤:我们那个初中教物理的就是牛津的,那个英文教员特别好,他不是跟你讲语文,他给你讲修辞学,水平特别高,可惜我们当时水平太低。那个教国文的先生是黄侃的学生,这样好的教员。
解说:根据刘敬坤的回忆,在西迁之前整个湘西只有一所很小的中学,而教育系统的西迁首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原本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大批青年能够在战乱中继续学业。陈立夫在1938年1月成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在任期间国民政府改写了“中央向来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国民政府规定,抗战期间学生的学杂费一律免收,而且吃饭不要钱,这对于沦陷区来的学生是最大的福音。
刘敬坤:抗战8年中间,全是公费,如果不是公费我们能念书吗?大学继续招生,而且大学规模都扩大了。你想,抗战前二十几年只有五六万大学毕业生,那时候一个大学的规模都是很小的,而抗战后一下子就出来五六万、六七万大学毕业的学生,这是中国很大的一笔智力财富。我有时候讲抗战8年,国民党打仗那个事情我们且不讲,国民党就从这一点来讲不能否定人家,那么样一个国家,那么困难的时候,人家没有停止办学。我有个亲戚在台湾,他后来回来,他说,台湾就靠我们在大陆上去的那些人,他讲,我们去的无论如何没有留在大陆上的人多,可是你们都没有得到用。这话讲得很实在。
解说:六十七年前刘敬坤十五岁,那一年,他在偏僻的西南山区享受到了读书的乐趣。1938年10月底,学校派人辗转三千里把“图书馆”运到了湘西。在学校的图书馆,刘敬坤看到了《大公报》,看到了《新青年》,也看到胡适、陈独秀以及毛泽东的文章。可是书读得多了之后,刘敬坤却上了学校的“黑名单”。从1938年10月开始,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仅审查各地的图书出版,对于阅读所谓违禁书籍的学生也要严密检查。这时,陈立夫的老部下邵华成为国立八中的校长,刘敬坤不久就成了邵华眼中的问题学生。1943年,刘敬坤接到了勒令退学的通知。
刘敬坤:那个训导主任很好,训导主任讲学校里也不挂牌开除你,邵校长讲了,你自己退学走吧。他总共给我200块钱,给我写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印维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专管跟共产党作对的;还有一封给国民党中宣部的原副部长方治,他从前给他当秘书;还有一封给一个姓吴的。我就拿着这三封信到重庆了,到了重庆还剩7块钱。
解说:无奈之中,刘敬坤只好硬着头皮去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方治。
刘敬坤:我也不知道方治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多大的官。他的屋子外面还有一间屋子,有个佣人给看着,坐了一排,有的着军服,有的穿着西装,有的穿长袍大褂,都是很阔气的。他讲你坐到最后啊,我就坐到最后了。方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过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他一个一个会客,都走了以后我就进去。他一看我穿个草鞋,穿个短裤,他看见我先生的信了,不满现实,他说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你念书去。我想开除了怎么念书。我叫你念书嘛。过了一会儿,他给我一个小条子,这么长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教育部赵英杰,与来人一谈,也没有写名字。他说你没吃饭吧,我讲没吃,那你就吃我的。他在那个办公室有晚上办公的工作餐,一碗饭、一盘菜、一盘汤。他说你就在我这吃吧,我出去吃。吃完了,出来以后我就问请问方先生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你看看牌子。我一看牌子,中国国民党总裁室。我的妈呀,我恐怕是在总裁室里面吃饭的唯一一个人,他就是总裁室秘书,就代表老蒋接见那些人。
解说:口袋里揣着方治给的20元钱,凭借着方治写的一张字条,刘敬坤顺利进入了教育部主办的流亡学生进修班。
刘敬坤: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学院罗刚写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行》,我看了以后觉得三民主义怪有道理。一个上海的学生,我记得他天天唱那个《秋水伊人》,他桌子上摆了一本书,我翻了一翻,也不知道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看,正是批判我欣赏的三民主义的。哎哟,我就拿笔和纸抄,我抄了几遍了,有好多句子我都能背上来,都能成段地背。《新民主主义论》,我觉得这个路好,这个路子对。其实那时候理解力也不怎么样,我觉得最后一句,什么“太阳快要升起,让我们双手迎接吧”,那个文章写得气势好,一泻到底,那个文章写得确实有气势。
解说:不久之后刘敬坤离开流亡学生进修班,来到了国立第九中学。然而立足未稳的他却因为参与罢考再次被迫离开了学校。刘敬坤只好和好友一起偷偷来到位于重庆沙平坝的国立中央大学,在这里,他们除了“偷师”,还要“偷饭”。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22岁的刘敬坤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他就读时候的中央大学被称为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学府,他入学时这所大学的招生比例是二十比一。抗战8年刘敬坤没穿过袜子,当他穿着麻草鞋、背着简单的行李走进报到处的时候,工作人员把他当成了挑夫。
刘敬坤:如果不是公费,我们能念书吗?全是公费,大学继续招生,而且大学规模都扩大了,中央大学抗战前只有1500人,7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教育,7个学院,只有1500人,到我进校的时候,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到3500人了。
解说:根据刘敬坤的研究,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大学毕业生大约有5到8万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抗战之前所有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总和,许多高校在艰苦的战争期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国立中央大学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敬坤:现在都讲北大怎么样,当时中央大学跟北京、联大是对劈的,它是一个系科最完备的大学,中国没有第二个大学有这么完备的系科。而且它规模最大,人才进去很多,它对中国近代学说是有贡献的,哪几个贡献?一个是生物学,中国生物学最有名的胡先骕。还有一个地学,地理、地质、气象,这里面就是竺可桢竺先生。历史,沈刚伯在中国近代讲外国史是最早的,可会讲了,上课你两个耳朵就听着,根本就不记笔记了,那真是袅袅动人啊。我们念书的时候徐悲鸿还在中央大学,徐悲鸿这个人可是很好。
解说:刘敬坤入学的时候正是国共重庆谈判的进程当中。1945年9月6号,毛泽东突然来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教授宿舍。
刘敬坤:毛泽东到中央大学去看他一个老同学,叫熊子容,是教育系的一个教授。那一天他坐一个吉普车,我们都在饭厅里吃饭,只听说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朝门口挤。我跑到那个门口,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穿一个灰布中山装,他还讲“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好”,还从那个汽车里面说“中央大学同学们好”。还有周恩来,周恩来也看到了。
解说:刘敬坤说,当他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在他看来,当时的左派学生们都有一种简单而坚定的立场,那就是一切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他们就会坚决维护,反之则坚决抵制。刘敬坤在重庆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刘敬坤的印象里,当时同学中倾向于共产党的人还是少数,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彼此之间经常公开辩论。
刘敬坤:我们经常在重庆沙平坝茶馆聚会。我们同学中我是《新华日报》立场,还有几个是《中央日报》立场——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还有的是《大公报》立场。到茶馆里去,《大公报》立场的人就根据《大公报》的立场来讲话,《新华日报》的立场的人就根据《新华日报》来讲,《中央日报》的就在那里公开骂,骂到最后呢,都是《大公报》的那个人讲:好好好,今天就谈到这么多。由《大公报》的那个人出钱——坐茶馆要给钱,好了,明天再来。那真是民主得很。在那个茶馆里面,我们就各摆各的道理,有个国民党的人就讲,我们现在不要按系上课了,按照党派上课吧,居然说这样的话。在1946年的重庆,很民主的。
解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力量曾经遭遇了极大的破坏。当时中共党内负责国统区工作的周恩来,通过武汉长江局,也就是后来在重庆的南方局,逐渐发展出三支新的学生力量,分别是以重庆的中央大学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以昆明的西南联大为中心的民主青年同盟,还有以成都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刘敬坤认为正是这三支民主力量,和上海孤岛时期的地下党组织,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共同组成了抗战以后强大的民主力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1946年11月1号,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然而仅仅半年之后,1947年的5月20号,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南京大学生就发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内战、所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游行发生三天之后,新华社发表评论说“这次群众运动的规模气概为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有”。1947年5月30号,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名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文章,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有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文中的“学生运动”,就是指十天前发生的“五.二〇”运动。
刘敬坤:5月20号就游行了。我们走到朱家路口,第一道是警察,第二道是宪兵,第三道是骑兵,把队伍堵了,弄了个高压水龙头冲,我一下被冲到地下坐着,另外一个同学把我一拉。警察拿的是木棍,那种指挥棒,一头蓝,一头白的,就拿那个东西打,也打伤几个人。宪兵有武器,马队都是蒙古的大马,但没有开枪。结果我们过不来,我们都走小路转过来,等到过了那个防线以后又集合起来。正好那天要下雨,我们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后来我们跟他协商了,就是我们这个自治会的主席跟那个参政会的秘书长,就是邵力子跟他讲好了,不喊口号可以回到学校,结果我们在那以后没喊口号,没唱歌,就回到学校里来了。5.20之后那就厉害了,国民党就镇压了。
解说:与毛泽东的论述不同,刘敬坤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研究,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并非“第二条战线”,而是“第一条战线”。民主运动从政治上打败了国民政府,从而使解放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刘敬坤简介:
刘敬坤,1923年11月26日出生于安徽霍邱县。1929年至1936年2月,在家乡读私塾和高小。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在阜阳读初中。1937年12月13日,日寇攻陷南京,他以三尺稚童,即萌执干戈以卫家国之志。1938年8月日军进逼安徽,他别父老,辞故园,随校南迁,敝屐蓑衣,徒步千里,翻山岭,涉江湖,辗转湖北、湖南。在湖南永绥国立第八中学读书期间,因阅读《新华日报》和进步图书,被校方劝退离校,漂零流徙,辗转至渝。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重庆工事参谋团任少尉,但在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劣迹后,他萌生了反抗思想。1945年10月,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因深恶痛绝国民党之独裁,复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感召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参加了重庆大中学生“一二五”游行。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先后参加了1947年1月的学生反美暴行游行,同年的5月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成为民主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47年10月转入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学习。1948年5月参加了进步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任小组长。在任《中大周报》、《大学评论》兼职编辑期间,及时反映学生运动情况和党组织的声音。1948年7月,在中央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初国民党溃退前,参与组织并参加了中央大学应变护校斗争及“四一”学生请愿救人游行,为南京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建国后,他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6月在中央大学毕业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教育干事,1951年6月任南京市宗教事务处秘书,1952年9月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教员,1955年3月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员,1956年5月任讲师。1957年12月因直言陈词,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4年,席地食草,饥寒交迫,受到极不公正对待。1961年11月,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乃抱病痛之躯,重返工作岗位。1962年8月后,他先后被安排到南京农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图书馆和农业机械化分院、镇江农机学院图书馆任管理员。在此次期间,他不怨天尤人,没有消沉,而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深信党组织会对他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他酷爱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
1979年7月,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关于右派分子刘敬坤的结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恢复讲师职称。1981年6月,通过严格考试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12月离休。刘敬坤对中华民国史进行了深入探索,于近代租界、近代高等教育、中华民国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抗日战争史等领域均有精到见解,为中华民国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他一生阅历丰富,熟稔民国掌故人物。离休后,他仍然坚持学术研究,钩沉索引,笔耕不辍。先后发表《关于我国近代租界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回顾》、《我国历代国防形势与抗日战争全盘大战略的研究》、《关于淞沪会战两个问题的探讨》、《抗战中的中央大学》等论文与文章数十篇,主持译校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等,其扎实成果和严谨学风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刘敬坤一生坎坷,历经困苦磨难。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投身革命,坚持信仰,努力工作。1978年后,他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性格耿直,谦虚谨慎,严于律己,诚恳笃实,团结同志,乐于奉献,赢得了所内外同志的尊敬与爱戴。2009年5月6日刘敬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相关链接:
2025-03-20 23:15:10 |
|
|
[3楼]:
这位网友你去跟河南人说,看他们可骂你,怎么不让豫东水把你喝饱淹死 |
|
2025-03-20 23:12:56 |
|
|
[2楼]:
那个你怎么自己不喝黄河水?你知道当时中国的处境吗?你是要被淹死吗? |
|
2024-06-08 21:03:20 |
|
|
[1楼]:
鉴定为:黄河水喝的太饱导致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