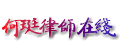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盛况之后的文学
1428 人阅读 日期:2008-11-15 16:06:52 作者/来源:京华时报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席卷中国。《人民文学》、《收获》这些纯文学期刊,都达到了百万份的发行量。
如果考虑到文革后,中国人贫乏的精神生活中,最先开禁的是纯文学,就可以理解,文学这种奢侈的精神生活为何变得如此大众。
多年后,当娱乐和大众传媒兴起后,当年文学的盛况不再已成必然。那些留下来的读者,也是真正的欣赏者,文学就此回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
70年代
文学的匮乏时代
每天中午12点半,父母忙着张罗午饭,李敬泽拧开收音机,一个熟悉的男中音用煞有介事的语调,开始讲述村支书萧长春的故事。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经常出现在李敬泽家的一幅场景。
童蒙初开的李敬泽知道,萧长春是个好人,但他对这个严肃无趣的好人实在没什么印象。真正吸引他的,是这部名为《艳阳天》的小说里一帮被鄙视被贬损的反面人物:马小辫、弯弯绕、马大炮……
2008年2月,小说作者浩然辞世,身为《人民文学》副主编的李敬泽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将他早年这段文学接受史称作“小说史上一个壮丽而恐怖的时刻”:世上的小说和故事都被严厉禁止,一个叫浩然的人的讲述被亿万人倾听。
李敬泽是幸运的,因为母亲在出版社工作,在《艳阳天》、《虹南作战史》等少数当时出版的“大路货”之外,他有机会看到母亲通过一些渠道搜罗到的别人难得一见的书。
李敬泽记得他上小学一二年级就看过《红楼梦》,那好像是母亲通过某种关系从造纸厂淘出来的,“那时要说谁家有套《红楼梦》,这事儿很大!”
上中学后,母亲供职的出版社那个大得像书库的资料室让李敬泽大开眼界,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基本上都有。这导致李敬泽上大学前没怎么认真上过课,大部分时间都在“乱看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然在必读书目之列,他曾把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名言抄下来:“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然而多年后,他说自己一闭眼就能想起来的,是那个穿着海魂衫在树林里像个小妖精一样奔跑的冬妮娅。“当时看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肯定不靠谱,可我后来问过好多同龄人,大家提起来都是一拍大腿:呀,我记得也是这个!”
“那时谈个恋爱都要正襟危坐,李敬泽同志,我觉得今天我们俩可以怎么怎么样了——都僵硬到这个程度,但你在冬妮娅身上看到什么叫人性之美,什么叫生动,什么叫生命。”李敬泽说,即便在那个年代,人们凭直觉最容易领悟的,仍是那些最富人性的东西。
回顾早年阅读经历,李敬泽说文学之所以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至深,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文学可能是惟一的一道光:“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讲,他知道世界有多么大,他知道世界有多么丰富,他知道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生活还有多么广阔的可能,几乎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偶尔落到他手里的一本书。”
80年代初
《收获》发行过百万
1977年底的一天,已经读初三的李敬泽走在街上,回荡在城市上空的高音喇叭正在讲述一个名叫谢惠敏的“好孩子”和一个名叫宋宝琦的“坏孩子”的故事。
李敬泽记得那时一开会,高音喇叭就宣读社论、播报重大新闻,有时也会播一些小说,他正是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了刘心武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以此为发轫,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纪元正式开启。
十年浩劫十年噤声,重获新生的人们有太多话要说。然而失语太久,那最初的呐喊艰难沉重、探头探脑。
将近一年后,才从上海传来一声呼应:1978年8月,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习作《伤痕》,在《文汇报》发表。据当事人回忆,无论《人民文学》还是《文汇报》,刊发这两篇作品都有过长时间的犹疑和争议。
闸门一旦开启,洪水滔滔势不可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审美之堤。
在这接踵而至的浪潮中,文学期刊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短短几年,先后复刊、创刊且有全国影响的期刊就有《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诗刊》、《星星》、《世界文学》等数十家,省级以上期刊超过200种。
据《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介绍,上世纪80年代初,这本老牌文学双月刊发行量曾高达100多万份,这让当时的主编巴金颇为担忧,“巴金有非常丰富的办刊经验,他知道这个现象不正常,满大街全是你的杂志,这是很可怕的。他说100万份太高,宁可少印一些。”
大学校园同样是这股文学热潮的重要阵地,文学社团遍地开花。诗人徐敬亚称,到1986年他策划“现代诗群体大展”时,全国光诗社就有2000多家,“自谓诗人”百十倍于此数。校园之外,人们对文学也是热度不减。由建筑工人北岛、待业青年顾城、纺织女工舒婷等人支撑的油印本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校园内外都受到追捧。
1984年,北岛前往成都参加“星星诗歌节”,实实在在领教了一把四川人的疯狂: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他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了灯,缩在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多年之后北岛写道:“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这种狂热就不复存在了。”
正是在这样的狂热气氛中,1980年夏,16岁的李敬泽考入北大中文系,从石家庄北上一脚踏入燕园,发现同学个个都是“诗人”。
不惟中文系如此,在其他专业,文学青年亦比比皆是。与李敬泽同龄的诗人海子比他早一年来到未名湖畔,这名来自安徽乡下的天才少年,就是从北大法律系出发,划出了一道炫目而转瞬即逝的生命弧线。
80年代中后期
稿子用否都是大事
李敬泽说现在回想起来都不知道北大四年是怎么过来的,那时大伙文学热情高涨,几乎每个人都在写诗,就他不是文学青年。
虽然看了很多书,那时他没想过自己要干文学这一行,没写过诗,连散文都没写过,“我在宿舍睡上铺,晚上经常听他们在下铺争论,这诗应该这么写,那诗写得好,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李敬泽将个中原因归结于自己年龄太小,那会儿他们班长40多岁,完全两代人,“我当时基本上就是一小孩儿,懂什么呀?就是跟着混的那一拨。”
1984年大学毕业时,李敬泽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解放军某总部,一个是去《小说选刊》做编辑,一想到穿上军装每天要出早操不让睡懒觉,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在地安门附近一个院子里,20岁的李敬泽开始学做“二道贩子”。李敬泽说,那时某个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了,政治上有没有问题,艺术价值如何,《小说选刊》的取舍,常常是一个风向标。
1986年3月,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发表,李敬泽看后觉得很好,但当时的领导决定不选。正巧那时杂志换帅,小说家李国文走马上任,李敬泽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下。这名新主编马上开会,决定把其他稿子撤下来,重新把《红高粱》选上去。
那是一个令李敬泽回想起来仍兴奋难抑的年代,不断有新东西出现,都是你以前的理解力和感受力所达不到的东西,“经常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作品往那儿一放,哇!爆炸性的。好嘛,然后就是激烈的争论。当时觉得一个稿子用还是不用都是大事儿。”
的确,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坛奇峰迭起的年代,在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兴起的同时,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等年轻作家以鲜明的先锋姿态登台亮相。“写什么”不再那么重要,“怎么写”被突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
禁锢太久,人们求新求变的热情超乎想象。短短几年间,西方一二百年来各种现代、后现代文学流派,几乎无一遗漏都被学习、操练了一遍。
乱花渐欲迷人眼,每天在热闹非凡的文学刊物间寻寻觅觅,李敬泽在《小说选刊》待了六年,“无可救药地变成了一个文学人。”
90年代
小说进入全盛期
1990年底,李敬泽调任《人民文学》编辑,2008年5月升任主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评论。
他的评论不太讲究学理是否严谨,更像随笔美文。与人私下交谈,这个善饮的山西男人更是机智风趣,毫不避讳京骂俗语。随着他在《人民文学》的升迁和作为批评家的声名日隆,一个段子在文坛流传颇广:年轻作家到京必做三件事——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有趣的是,在他之前,著名编辑家李陀和李敬泽在《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朱伟也曾享有类似声誉。
李敬泽说,狂飙突进的80年代过去之后,90年代文学确实缺乏80年代那样的创造光芒,整个时代气氛发生了很大变化,“80年代人人以文学为荣,到了90年代,人人以埋汰文学为荣。”但他认为,90年代以来文学依然有它自身的成就和进展,就普遍的艺术水准来说,在80年代基础上有相当大的提高。
在李敬泽看来,80年代文学之所以那样光芒四射,和当时的特殊语境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重复,“你没有办法让文学在90年代或现在继续保持80年代那种劲头儿。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地位的这种变化正说明了中国的长进、时代的发展。”
“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怎么自我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恨、我们的嘲讽,怎么像王朔一样骂人,怎么在语言中找到自由和娱乐,很大程度上都是文学开拓出来的。此前我们只有政治语言,没有别的。”李敬泽说,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有这样的机会,能如此强有力、如此明显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生活,这是新时期文学最值得骄傲的成就。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同样感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文学之外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文坛开始风平浪静。
不过这位被贾平凹称作新时期小说革命“最早的鼓吹者和实践者”的著名编辑家认为,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开花”,“结果”却在90年代。贾平凹、陈忠实、张承志、张炜等大批实力派作家的代表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10多年间,这些文坛精英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小说全盛时代。
这个温文优雅、平和谦逊的上海男人语出惊人:“只有历史上的唐朝诗歌,可以和这个时期的小说媲美。”
90年代后期
文坛进入萧条期
1998年的一天,李敬泽和《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青年评论家施战军聚首香山,商量推出一批“70后”作家,计划在《作家》发个专号,同时在《人民文学》陆续发一批。三人掐指算算账,全是女孩子。
“等到《作家》发那个专号的时候,每个女孩子都是弄出一个被人嘲讽的艺术照。然后我们就眼瞅着一个文学事件迅速变成一个非文学事件。”10年后回首此事,李敬泽结合文学圈外几个大事件,将1998年认定为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拐点。
那一年,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开始全国走红,娱乐精神成了文化领域中心性的东西。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网络门户元年”:四通利方摇身变成新浪网、网易突破电子邮件领域进军门户、搜狐老板张朝阳入围《时代周刊》全球数字英雄榜。
“网络由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技术,忽然成了我们的一个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基本上是从1998年开始的。”李敬泽说,后来榕树下等原创文学网站创立,写作权利、语言权利都大规模向民众扩散,文学不再是一个高度精英的事业,作家也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李敬泽称这些变化背后,是一套新的文化逻辑的确立,作家对文学本身的看法已然改变,“之前很少有作家认为这事儿是个买卖,1998年之后,所有作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买卖:读者很重要,市场很重要,炒作很重要。”
李敬泽说如今再以文学中心论者自居缅怀上世纪80年代没有意义,他只关心在当今环境下,怎样才能保持文学的影响力,使文学依然成为我们文化中一种活跃的、富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命题。
比李敬泽年长六岁的程永新说,进入新世纪,他常常有些焦虑,“可能也是人到中年的缘故吧。”他感到文坛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萧条期。
一方面,除贾平凹、迟子建、莫言等少数作家仍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外,一大批重量级的优秀作家陷入了写作困境,想超越他们自己似乎没有可能。年轻一点的如东北的金仁顺,近年有不错的作品问世,但没有一个群体能延续90年代的繁荣。
更加年轻的如韩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写作者”,他们的“青春读物”发行量很大,但这些人根本不认为要把一个什么文学传统继承下去,“你根本不能指望他们认同你曾经有过的辉煌,韩寒就是这个态度,到处骂人。”程永新说,这样的局面导致文坛青黄不接,出现了一个文化的大峡谷。
在程永新看来,文学的边缘化无可逆转,现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平庸。他认为每个时代的文学都要有先锋性在里面,“这种先锋性不是说你的小说没人看得懂,而是你的精神思索、艺术追求永远走在常人前面,走在生活前面。”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南北辉映的两大重镇,《收获》和《人民文学》的发行量都曾上百万。如今前者发行量为十二三万,后者六七万,对于这个数字,程永新和李敬泽都觉得很正常。
“80年代你说有什么啊?没这么多杂志,没网络,看个电视还得去邻居家,可不就是一本文学期刊呗。我是不再梦想80年代的盛况了,除非社会大倒退,把网络关了,电视关了。那世界不是太可怕了吗?”2008年深秋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坐在北京东三环边的办公室里,李敬泽点燃烟斗,烟雾氤氲中如是说。
口述实录
《伤痕》发表前后
-口述人:卢新华
-身份:作家
要说起来我和你们报社还是有点缘分的。我大学毕业时,因为是党员,退伍军人,又是上海市青联常委,中国作协会员,就业前景很好。其中最诱人的去向就是《人民日报》社要我去做团委书记。
当时学校管分配的老师一共找我谈过三次话,前两次我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愿意去的态度。最后一次他动员我:卢新华,你知道《人民日报》社团委书记是个什么概念吗?如果外放,就是个地委书记!
这对我的诱惑力确实是很大的,我从部队退伍时不过是个侦察班长。但我思前想后,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当不了官。再说我希望有一种比较自由的生活。所以,最后去《文汇报》当了一名记者。
《伤痕》是我上大一时的一篇习作。作为响当当的红五类,我并没有《伤痕》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但我在现实中确实看到过、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伤痕”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
作为恢复高考后首批录取的大学生,我那时刚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们意气风发,成立了几个兴趣小组,我写过诗,理所当然被分到诗歌组,后来才“跳槽”到小说组。
当时班级要办一期墙报,每人必须根据自己所在兴趣小组交一篇相应的作品。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写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框架大致是写一个女青年,在母亲被四人帮打成“叛徒”后信以为真,选择与家庭决裂。在与家人断绝联系的9年里,她在革命、狂热和继之而来的消沉、挣扎、孤独、彷徨中煎熬。恋人由于她的家庭问题不能上大学,两人被迫中止交往。最后历史和她开了一个玩笑,粉碎四人帮之后,她才知道母亲蒙冤。在经历一番内心的忏悔和挣扎后,她赶回家中,不料刚获平反的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这个王晓华完全是个虚构的人物,不过她的模样是根据我当时的恋人、现在的妻子描摹的,稿子最后也是在她家小阁楼上一台缝纫机上写好的。那天晚上一口气写到凌晨两点,扔下笔才发现自己哭成了泪人。
后来,这篇习作经过我们小说组组长倪镳之手,贴到了班级墙报的头条。我当时把小说交出去后并没放在心上,两三天后的清早,忽然听见宿舍门口人声嘈杂,打开门探头一看,原来很多人正围着看我那17张稿纸的《伤痕》。
以后一连好几天,墙报栏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还有同学边看边抄,泪水不断洒落在笔记本上。直到《伤痕》在《文汇报》上发表,墙报栏前读者始终络绎不绝。众人对着墙报伤心流泪,成了复旦一景。
《文汇报》记者听说这事后,就托人找我要稿子。但稿子4个月之后才见报,中间过程很曲折,当时发表这样的作品,报社也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作品。《伤痕》给我的命运带来的转折,却让我始料不及。
就在那一年,还在读大一的我,成了文革后首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随后,我又被推举为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那个时期,我频繁出席活动、参加会议,受到过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到学校,还经常一周两次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外记者。
当掌声、鲜花、荣誉一齐涌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我只不过是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中了一张“彩票”。
《伤痕》发表后,有很多文章说它突破了这个禁区,突破了那个禁区,陈荒煤啊、王朝闻啊,很多大理论家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其实我想说,我什么突破都没有。
他们看到的突破是从文革这一段看的,文革时期把什么都弄得没法写了,三突出啊、高大全啊,纯粹成了八股,我对于文革时期确实是有许多突破,爱情的禁区、悲剧的禁区,什么都是突破。
可是要是对照二三十年代——鲁迅的年代,我一点突破也没有,对照19世纪契珂夫、莫泊桑的时代,也没有任何突破,充其量继承了他们一点文风。其实我写《伤痕》之前想的就是,我要回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传统。我在文革期间没写过什么东西,所以他们看了觉得不一样,很清新,其实还是很拙劣的,跟那些大作家相比,显得很稚嫩。
新时期文学大事记
□1977年
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先声。
□1978年,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举行,作协等5个协会正式恢复工作。
□1979年
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京举行,会议重申双百方针,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2年
首届茅盾文学奖颁出,《芙蓉镇》等6部小说获奖。该奖项至今年已举行7次颁奖,获奖作品31部。
□1986年
11月,中国作协设立综合性文学大奖——鲁迅文学奖。
□1999年
《萌芽》杂志与北大、复旦等高校联合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等少年作家开始崭露头角。
□2006年
11月,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接替于2005年10月病逝的巴金,成为继茅盾和巴金之后中国作协历史上第三任主席。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