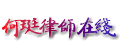翻译回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吵的内幕
1874 人阅读 日期:2008-06-08 17:26:11 作者/来源:阎明复
核心提示:阎明复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有幸亲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最近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回忆录,重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世界上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列席大会。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秘书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人,他能用俄文交流。
9月23日,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明天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转告客人。第一次有幸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给他当翻译。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年轻翻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我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和不安。听说他老人家乡音极重,我能不能听懂他的湖南话呢?他会同南斯拉夫客人谈些什么呢?碰到生僻的词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困扰着我,当天夜里几乎一直没合眼。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会见就安排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达会客室时,只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着宽绰的浅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头的黄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绍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后,我正准备随客人一起走进会客室,毛主常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亲切的话语,立刻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时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见,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一些,我知道他精通俄文,翻不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南关系到中苏关系,还谈到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老人家浓重的湘音,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一下子很难找到对应的俄文。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当主席讲“盲动主义”时,我犹豫着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壳”了,便轻声用俄文提醒说“ПУТчИЗМ”。他帮我一次次摆脱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泽的任务。
1957年1月,中办成立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我担任组长,另外两位是朱瑞真和赵仲元。尚昆曾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个小外事机构,指的就是这个中办翻译组。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的事情,既不找外交部,也不找中联部,都由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处理。
翻译组成立后,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尚昆同志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主席对当前重大国内外问题的观点,熟悉毛主席的习惯用语,让我们能有所准备,在毛主席和外宾谈话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毛主席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怕我们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毛主席常用词、词组和成语三大本汇编送给我们,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随毛主席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1月2日,代表团乘苏联派来的图104专机赴莫斯科。起飞不久,我到前舱向主席报告一些事项。主席坐在机舱右侧书桌的后面,对面坐的是副委员长宋庆龄,彭德怀同志坐在左侧的沙发床边。我走到主席跟前,正要向他报告,主席问宋庆龄说:“你认识阎宝航同志吗?”
宋庆龄说:“认识,很熟。”
“阎宝航是好人!”主席说着,指着我向宋庆龄介绍道,“他叫阎明复,是宝航同志的儿子,是俄文翻译。”
这时,主席发现我站在彭总的前面,把彭总给挡住了,就对我说:“你这个人呀,怎么把大元帅遮住了呀!”
我赶快站到一边,向彭总道歉,彭总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呀!”
专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在伊尔库茨克稍作停留。伊尔库茨克这年冬天来得早,已经下了一场雪。毛泽东惊奇地发现,机场附近有一片庄稼长得绿油油的。他便问地方领导人:这是什么庄稼,现在还在开花?地方领导人回答说,这是“РОЖь(罗什)”,我们几个翻译都不知道这个词,有的说是“大麦”,有的说是“荞麦”,毛主席都一一否定了,说这个季节不可能长大麦、荞麦。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急忙走上前来说,这是做黑面包的一种麦子。毛主席听了点了点头。回到飞机上,我找出俄汉字典一查,原来“РОЖь”就是“黑麦”,于是带着字典走到前舱,对毛主席说,字典里写的是“黑麦”,刚才我们都翻译错了。毛主席听了笑着点点头。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毛主席住在捷列姆诺伊宫,这里曾是沙皇的寝宫。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工作人员都住在克里姆林宫。
我们刚安顿下来,忽然听到有人说,毛主席来看我们啦!于是大家都涌到走廊里。我们每个卧室门上都贴有名单。毛主席看到名单上“朱瑞真”三个字,便说,“这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呀”朱瑞真答说,“这是家里老人们起的名,可以改”。毛主席说:“不用改,就这样叫也很好嘛。”
毛主席觉得给他准备的原沙皇用的卧室太大,想调换稍小的一间。毛主席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好不好?”李越然跑去报告杨尚昆主任。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寝室……毛泽东终于做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
在苏方人员的配合下,根据毛泽东的生活习惯重新布置了他的卧室:把原来的笨重钢丝床撤掉,换上了一张宽大的木板床,把毛毯、鸭绒枕头之类的东西拿走,换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又长又宽的棉被和枕头,把卫生间的坐式马桶改成了蹲式马桶,调整了床头上的灯光等等。另外,苏方还为毛泽东在郊区安排了两栋别墅,供他需要休息时备用。
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因屡遭挫折,老子党作风有所收敛。
“大跃进”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
为了实现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的“在15年左右时间内赶超英国”的目标,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毛主席从莫斯科回来,连续召开了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在会上,他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批评了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
在这两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报刊上也开始出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跃进之类的新词。4月中旬的一天,苏联使馆二秘顾大寿突然打电话到中办翻译组,问最近中国报刊上出现的“大跃进”一词,应该如何翻译,把它译成“БОЛьШОИ СКАчОК”,对否?他接着说,为此事尤金大使批评了他。尤金认为,经济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循序渐进发展的,不可能跃进,尤其不可能“大跃进”。中国领导同志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一定是你们翻译搞错了。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问题,王稼祥指示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并指定由姜椿芳和我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派人到他办公室。朱瑞真和郑葵(徐葵?)去了,他还把正在北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去,共同研究会议文件俄文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翻译?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跳跃式地向前发展有点像兔子赛跑,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很难翻译。其他如“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等提法,也都有这样的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间,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当时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大家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摆出来,我们几个青年人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提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把柄。这时我们抓紧机会提出就“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20大后,他曾请示过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КУЛьТ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他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有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师哲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赫鲁晓夫感到担忧。他很害怕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便打破沉默,开始批评和挖苦。他还把保加利亚领导人召到莫斯科,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大跃进运动,否则不再向他们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争吵
1958年7月21日傍晚,苏联大使尤金来电说,他受赫鲁晓夫委托请求紧急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于当天晚上9时许接见了他,我担任翻译。
尤金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设一支共同舰队,苏联的自然条件使苏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长,四通八达。毛主席听后非常恼火,他质问尤金,你们是不是又要搞“合作社”否则就不帮助我们?尤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毛主席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第二次接见苏联尤金大使,直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毛主席说,看来,中国海军提出的关于建造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我们可能会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问题。毛主席越说越有气,他接着说,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口、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同他吵过嘛!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这次提出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如果讲条件,双方都不必谈。在谈话中,毛主席还谈到苏军方提出的在中国修建长波电台(雷达站)、在华苏联顾问工作中的问题以及对米高扬的意见等。
毛主席最后说,我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要么我到莫斯科去,要么他到北京来。
杨尚昆提醒我们,赫鲁晓夫来北京后很可能把责任推到尤金身上,说尤金把他的建议转达错了。我们也预感到中苏两国领导人将面临着一场大的争论。因此,我把李越然请来同我们翻译组一起参加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
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31日秘密到达北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一直把他接到怀仁堂,立即开始会谈。中方只有邓小平,苏方只有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参加。在会谈中,赫鲁晓夫一再强调:苏共中央从来没有提出过,也从来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这是个误会。是尤金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转达了我们的立场。关于长波电台问题,那是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苏共中央根本不知道。我们同意中方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你们建,归你们所有,我们可以使用,共同使用。毛主席说,关于“合作社”的问题这次讲清楚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会谈中赫鲁晓夫表示要撤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针对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意见,赫鲁晓夫也做了解释。本来为欢迎赫鲁晓夫安排了晚宴,会谈结束时,叶子龙走进会场向毛主席报告宴会准备好了,毛主席一摆手说,“不吃!”
这次会谈后,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于8月1、2、3日又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谈。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中国是秘密来的,但回去是公开的,临走时还发表了一个中苏联合公报。公报中有几句措词强硬的话,用毛主席的话说,那是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在这次中苏最高级领导人会谈中,虽然解决了关于共同舰队的争论问题,但我们感到,毛赫面对面的争吵却大大增加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以后的中苏关系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作者:阎明复 摘自《中华儿女》2007年第11期、12期)
相关链接:
2023-03-12 13:23:50 |
|
|
[3楼]:
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啦!说啥都硬气.让人民吃不饱穿不暖,没言论自由,说的再好?只有狗奴才信.骗不了全国人民. |
|
2022-12-02 14:35:22 |
|
|
[2楼]:
赫鲁晓夫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结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都失败啦!而且很惨. 饿死人民3700万.15年赶上 英国?现在赶上没? |
|
2022-06-06 11:36:16 |
|
|
[1楼]:
关于长波电台,以前我看一个刊物报道说:苏联出电台设备,中国出人管理.两国使用.我不懂对中国有哪些危害?可能当时考虑中国没有潜艇,用不着长波电台吧?但作为友好国家,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应该搞好关系,毕竟苏联援助我们,制造尖端武器.发展经济.美国在日本(俩国有深仇大恨).韩国台湾都驻过军,结国在亚洲这三个国家发展都快!自力更生总不如别人帮助发展来的快!(说的要不对请大家指正) |
|